资料来源:社會學會社
发布时间:2025年05月23日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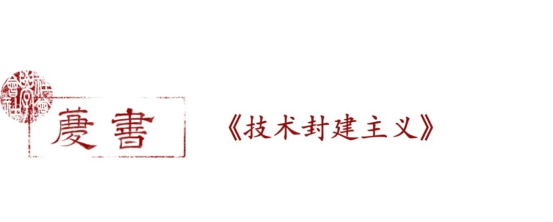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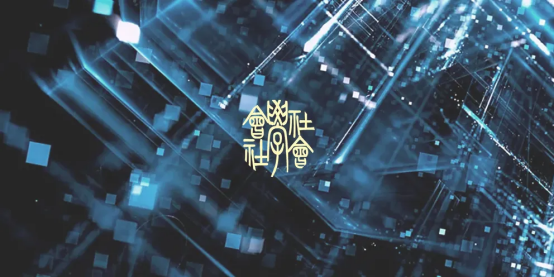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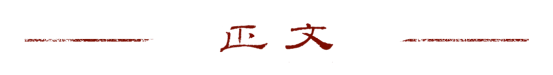
在技术加速、数据泛滥与平台垄断重构日常生活的今天,资本主义是否仍然维持其“旧有形态”,抑或正在滑向一种根本性变异?《技术封建主义》作者,法国政治经济学者塞德里克·迪朗,提出一种可能:我们正见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传统逻辑的新封建复辟。全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为何?利润动机如何与数字流动性相互作用?这种关系是否已引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质变?围绕这些问题,作者从意识形态、数字统治、无形资产与生产逻辑变迁四个维度展开分析。限于学识水平和篇幅长度,本文将按照上述行文框架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最后一部分进行粗浅评述,论述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谅解。
硅谷共识与加州意识形态的悖谬
“硅谷共识”是继二战后的凯恩斯共识、20世纪末的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资本主义政策工具。不同于“凯恩斯共识”强调财政政策对实现充分就业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热衷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紧缩政策,“硅谷共识”侧重于知识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它以加州经验为基础,并利用了这种经验传达的巨大想象力。加州意识形态是根植于政治激进主义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与加州企业精英自由市场信仰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的结合点则是技术乐观主义——对互联网技术解放潜力的乐观态度。嬉皮士社群在70年代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狂热追求是60年代反权威的社会运动的延续。这种狂热追求将技术赋予增强个体摆脱大企业和大政府,实现激进自主权的能力。随着凯恩斯共识的瓦解,反权威的嬉皮士社群文化与支持自由市场、强调的个人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拥抱,逐渐丧失其激进反抗的精神内核,成为支持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力量的资本主义保守文化。如同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硅谷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和发展,加州意识形态则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地方化变体。
迪朗指出,进入新世纪后,“硅谷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政策逻辑。它不再强调市场的静态配置效率,而是突出“创造性破坏”的动态效率,将“激励”作为核心议题,强调冷静的公共干预、企业家精神的释放、要素市场的灵活性以及对创新产权的保护。以此为支点,加州意识形态构建出一幅数字资本主义的繁荣神话:初创企业焕发结构活力,工作场所充满创造与自主,资源高度流动,经济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得以缓解,国家干预则日益退场。然而,这一套美好叙事与现实发展之间存在一系列悖论。
——初创企业要存活,就必须将掌握的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陷入资本集中化与中心化,以满足不断扩大增长的需求。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初创企业,并未实现经济结构的去中心化与开放竞争。相反,随着技术带来的生产结构变革逐渐沉淀,其发展路径仍遵循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趋势,直至形成新垄断格局。
——硅谷科技公司的现代化的办公环境与“自主创新”叙事塑造了一种“工作自由”的乌托邦,但是这种宽松自主表象背后是对劳动过程的加速控制。数字化工具让多数员工无法确定工作的目的和完整形式,过度活跃和无足轻重两种感觉交织涌现。信息通讯技术确实带来了技能增加和任务复杂化,但也同步加剧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规范化。

图为硅谷鸟瞰图。[图源:Wikipedia]
——硅谷的创新与活力被归纳为人才知识的自由流动与开放多元的文化。但地理经济学已表明,知识的聚集效应只会扩大而非缩小。即使开放的文化和人员流动性被赋予硅谷最初的决定性优势,促成它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知识生产领域优势的持续积累与放大。除了外部的地区极化,硅谷内部在经济、种族与性别层面的不平等依旧持续存在,且与其它地区相比更为显著。当区域经济的规模作用被忽视时,个体野心的自由度便被过于理想化,从而遮蔽了集聚效应所制造的不平等现实。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被用作正当化硅谷式创新的理论基石,但现实中却是“创新加速,增长停滞”的“无增长创新”现象。数字技术大量产出的是非商品化信息与用户行为数据,而非具备传统市场价值的产品,许多创新仅通过广告变现,导致经济重组而非扩张。这一过程并非“创造性破坏”,更近似于“破坏性创造”。
——欧洲对加州意识形态的盲目接受,将技术创新政策纳入市场自由化逻辑,忽视国家干预与战略投资,最终削弱了自身在科技产业中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韩等国家以国家干预和战略投入实现创新崛起。当加州意识形态鼓吹国家干预的退场时,硅谷的崛起乃至美国技术的发展史却与军工复合体的订单、航空航天领域的投入等公共干预密不可分。
在揭示“硅谷共识”所蕴含的一系列悖论的基础上,迪朗指出,数字技术并未带来一种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形态,反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的“倒退”。
数字统治的诞生:征服、捕获与控制
迪朗将数字平台扩张比作历史上的领土征服,指出这种扩张逻辑以捕获数据源为核心目标,即控制可以观察和捕获人类活动数据的空间。这种逻辑依托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质,并催生了网络商业化的新模式。广告定价机制从基于横幅浏览量,转向基于预期点击率的算法估值。提升预期点击率,成为数字企业持续优化算法监控和数据整合能力的强大动力,并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大数据以自动归纳的方式被不断生产,并建构出一种幻象——“数据提供真相,无需理论干扰”。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数字平台企业对大数据的利用,视为“监控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她认为,该系统的盈利逻辑是通过预测和修改人类行为,以创造收入和控制市场。这种逻辑颠覆了哈耶克和凯恩斯所强调的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将“可预测性”置于中心地位。在对可预测性的竞逐中,数字平台企业以各自的方式强化算法监控和价值创造机制。
迪朗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的理论存在理论局限。他援引了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对祖博夫理论的两点批评:(1)过于关注“监控资本主义”的监控属性,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2)过于强调自由主义个体的理性选择,忽视了集体维度的弊害。沿着这两点批评,迪朗从集体维度的弊害与资本主义新面貌两个维度,拆解数字统治的实质。
不同于祖博夫的自由主义原子论,迪朗认为数字平台企业的运作逻辑不仅仅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更是一种“内在超越性”的社会建构力量。个体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被平台聚合、运算、制度化,转化为一种集体层面的结构性力量,反过来再影响个体行为,成为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接着,迪朗从用户、劳动者和市场交易机制三个角度,揭示数字统治所具有资本主义新面貌。
第一,用户角度。平台成为了21世纪新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环境”。用户因为网络互补性(别人也在用)、路径依赖(已有数据、习惯)、个性化界面和退出成本等“自愿”依附于平台。这使平台对个体施加了持续的支配和塑造力。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构成了新的“数字依附关系”。尽管平台技术上具备开放可能性,但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其主动排斥互通性,使用户难以脱离。
第二,劳动者的角度。平台劳动者虽然表面上拥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性(例如时间选择、任务接受),但实际上他们处于由算法驱动的高度不对称的控制结构中。劳动过程在算法系统中被实时监控、评价与调度,劳动者对平台系统高度依赖,既无议价能力,也难以独立提供同等质量的服务。平台公司借此规避了雇主责任,却通过技术系统实现了更强的控制力。这种统治既是雇佣关系的去法律化,更是以技术和数据为中介的劳动控制形式。
第三,市场交易机制的角度。信任的缺乏是阻碍市场运作的关键。而平台则通过引入声誉系统,以量化反馈机制重建信任关系,使交易成为可能。用户评价成为可量化的资本,决定资源分配和交易资格。随着推荐算法的介入,“评价—推荐—交易”的链条被进一步自动化。平台既控制排名与曝光,也掌握解释机制,集交易场所提供者、规则设定者与执法者于一体,构建出一种“技术—市场—权力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
无形资产、租金机制与食利者阶层
无形资产是指知识产品,比如常见的技术手册、食谱、乐谱,亦或计算机代码、设计、程序等。不同于机器、建筑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具有非竞争性、可无限复制等特征。随着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急剧下降,这些资产的传播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介,其使用变得极为廉价与高效,非竞争性的特性得以充分释放,进而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要素,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流程的高度分化提供了可能,利润获取则为其提供了根本驱动。资本通过新的地理空间布局实现资本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最标准化和最容易控制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实现生产的地域错位和产业价值链的两极分化。这种全球产业链的价值两极化,不仅是分工原则的延续,更是知识垄断过程的表现。以无形资产为核心的知识垄断,集中并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的“意志”。
迪朗认为,以无形资产核心的知识垄断背后主要有四种逻辑不同的租金机制,即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动态创新租金。
——知识产权租金。该机制的基础是法律上的排他性权利(专利、版权、商标等)对知识的私有化控制。这类租金不依赖于生产活动,而是依赖于产权的控制,对他人使用该知识的行为收取费用。当产权门槛抬高,创新变成大企业的专属权利,创新激励转向“囤积与封锁”。例如,专利巨头持有成百上千项专利,仅为收租,而非自身实际使用。
——自然垄断租金。不同于法律垄断,自然垄断源于技术和组织层面的结构性约束,主要包括网络互补性、规模经济与沉没成本。网络互补性意味着,系统用户越多,其整体价值越高,如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系统;规模经济则指边际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递减;沉没投资则限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可能。这些特征导致市场趋于单一主体控制,从而形成技术上的垄断优势。
——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无形资产(如软件、数据、组织经验等)一旦完成初始投入,其复制和应用的边际成本极低,几乎可以无限复制。而有形资产(如工厂、机器、运输设施)即使存在规模效应,也受到物理耗损、材料成本、人工投入等约束,边际成本显著高于无形资产。结果是,在同一价值链中,无形资产密集型环节的平均成本随产量增长迅速下降,而有形资产密集型环节的成本上升更快。这种差异构成了级差地租的基础。
——动态创新租金。该机制的基础在于数据积累与控制。在现代研发过程中,数据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投入。数据积累高度集中在产业链整合者手中,比如沃尔玛、亚马逊、苹果等,通过物流系统、客户平台、供应链管理系统获取海量数据。供应商自身的数据被“返还”用于自我优化,而平台则“吸收”所有数据用于整体系统创新。企业在价值链中越是核心,就越能集中数据,越能够形成创新能力优势,使企业处于“滚雪球式”的动态垄断地位。
上述四种租金机制的共通点都是对信息和知识的控制。这种知识垄断促成数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在催生出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
从封建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就历史概念而言,封建主义主要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权力的混合性。统治关系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交织,体现在对人的统治与对土地的控制合二为一的“统治权”制度中;第二,集中占有与奢侈消费。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遵循“集中—消费”原则,农业扩张带来的收益由贵族阶层集中占有,并被用于非生产性的奢侈消费;第三,经济剥削的强制性。贵族以掠夺逻辑为基础,诉诸暴力手段进行经济剥削。
就社会经济形式而言,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生产者对部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第二,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权;第三,生产与剩余价值榨取之间的脱节,剥削的显著性。
基于对封建主义特征的勾勒,迪朗提出,对于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殊性在于,资本的获利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直接的劳动剥削,转向通过“捕获机制”对稀缺数字资源和平台位置实现垄断性收益。这种“地租逻辑”最终导向一种掠夺性模式,其本质不在于创造价值,而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占有。迪朗据此提出质问: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当整个经济体系的利润不再源于生产,而主要来自对他人价值的占有(如专利收费、平台佣金、数据控制)时,社会还能持续创造新的财富吗?若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地租”获取,而非用于实际生产,是否将引发增长停滞、社会不平等扩大等深层危机?在回应这些问题时,迪朗从马克思的视角转向凡勃伦的“掠夺”概念进行补充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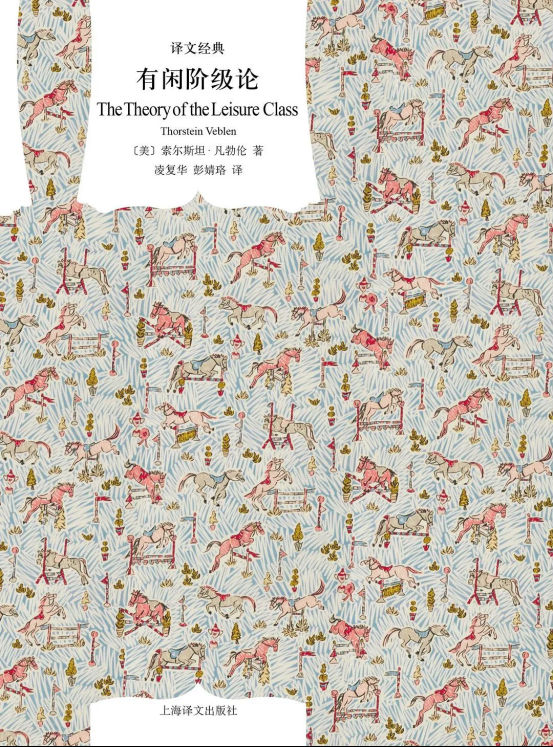
《有闲阶级论》,[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著,凌复华/彭婧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此书从金钱攀比动机出发,围绕着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这两种阶级行为特征展开分析,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探讨了有闲阶级的起源、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等。
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并不依靠生产获取财富,而是通过垄断、特权与占有来实现盈利,其经济逻辑具有显著的掠夺性。例如商誉(goodwill)——品牌、专利、信任或特许经营权等——虽能赋予资本个体优势,却并不创造社会整体财富。经济效率和创新不仅不会阻碍掠夺性规范兴起,反而经济越发达,掠夺空间越大。这构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前提。掠夺不同于寄生,它预设了一种统治关系:掠夺者在事前已确立对猎物的控制。这正是平台经济中用户与商家所面临的“狩猎模型”——在服务嵌入生活的同时,平台不断强化其支配地位。资本越来越多地投向维护和扩张对数字地租的控制权(如收购初创企业、构建算法壁垒),而非用于实际生产。
最后,迪朗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只是个开始,但是足以构成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挑战。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算法驱动的反馈循环天然地趋向中心化,任何去中心化的尝试反而被视为对使用价值的“破坏”。当代经济以“消费者效用”为核心逻辑,这一逻辑本身反而为平台的垄断性积累提供了合法性资源。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演化会推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进而为集体控制生产、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封建趋向,证实了这一社会化趋势。但方向却是资本主宰的无望时刻。资本通过算法和数据建立技术中介化的统治,组织和塑造劳动与消费过程。个体的主体性被算法治理的“去现实化”逻辑不断削弱。在这种逻辑下,人被简化为响应数据指令的自动机,剥夺其情感、判断与意志。
然而,人并非完全被动的存在。面对自动化推荐、标准化偏好与意义剥夺,人们仍会选择抵抗,比如拒绝自动化推荐、坚持自己的选择权、不愿放弃工作中的意义等。此外,生产活动之间日益紧密广泛的关联,也正孕育出一种解放的可能性——能使个体无限拓展其活动范围的力量。在迪朗看来,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山脊”之上:一侧是陡峭滑落的岩壁,另一侧则是通向解放希望的溪流与山谷。向何处前行,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方向选择。这一选择不在自由主义式的“技术乌托邦”,也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历史必然性”之中,而有赖于一种新的激进想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形式。
评述
数字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则提供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变迁的独特观察路径。迪朗提出:“我们究竟是仍然生活在一个糟糕的旧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生活在一个新的邪恶体系中?答案在经验上仍不确定,但最终取决于一个阈值问题。当挪用超过资本主义剥削时,体系就发生了变异。或者说,它已经发生了变异?”
这种对“变异”的判断并非随意发散,而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主线,结合凡勃伦关于“掠夺”的分析,并与当代数字经济批判理论展开系统对话,构成了本书的理论脉络与核心观点。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地租”成为关键概念。前文所述的“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与“动态创新租金”,正是数字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方式。对无形资产的产权保护与数据的滚雪球式积累,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演化为“新封建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用户、数据和平台充当起农奴、贡赋和领地。掠夺、租金、食利者逐渐取代剥削、利润、资本家,构成新经济逻辑。
然而,技术封建主义仍是一个假设,而非资本主义终结的断言。它更像是资本主义的“雅努斯面具”:表面呈现封建性(依附关系、租金机制),内核仍延续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剩余价值生产与私有制)(周亦垚等,2024)。不可否认的是,迪朗以“地租”解释平台经济的积累机制,并借“技术封建主义”的譬喻描绘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具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
此外,我认为本书另一个有价值却容易被忽视的点,是作者对数字经济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考察和解构。迪朗在开篇用大量篇幅,对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的流变历程的梳理分析,揭示这种高度集中化的、加剧不平等的乃至调挑战既有合法制度的经济形式,如何以进步、自由、创新和人性化的形象获得大众的广泛接受。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应用最后渗透至日常生活,所改变的不仅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透过各种论述和文化入侵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许怡,2023)。因此,对于任何单向度的技术叙事有必要保持警惕,并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以便能够看到被遮蔽的政治、社会权力关系。
最后,我认为文中的部分观点也存在可商榷或可补充之处。迪朗自述,“我一直称之为‘技术封建’的症状,意味着世界体系层面的生产僵局,资本回报不再能够通过生产基本大众商品获得,而是需要政治干预——保障垄断、承保投机性金融化等等(Cédric Durand,2022)。”首先,资本回报不再依赖生产大众商品获得,不等于生产僵局,而是进入新的生产性逻辑。实体投资情况存在国别分化,不能一概而论。仍有大量投资仍流入新能源、生物技术、半导体制造等非数字平台领域。数字领域投资本身也在重塑生产结构,如智能制造、数字孪生等在成为新一轮“生产性变革”。
其次,数字平台企业以平台垄断取代市场竞争,忽视了平台的二重性——既是企业也是平台(张兆曙,2022)。这种二重性以企业平台为边界分割出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在外,数字平台依然企业主体,面对市场竞争机制,承担运营成本和利润压力。在内,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型市场,发挥着提供规则、分发流量和扮演信任中介的作用,的确有强大的控制权力。数字平台体现的是市场—垄断混合结构,而非完全“封建化”。
最后,书中对算法技术和数据积累的作用过于强调,忽视或简化数字企业在技术大规模应用过程中与具体制度的互动复杂性。迪朗在书中引述,“从谷歌到优步和脸书,硅谷公司毫不犹豫地在一切法律框架之外形式,甚至违背现有规则,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加自己的创新。”事实上,平台的组织形式调整与合法性获得,始终需要监管政策的互动,存在抵抗、接受到落实的过程(赵磊等,2024)。平台企业实现稳定持续运营,所依赖的也不仅仅是算法技术和数据,同样需要嵌入在具体的用工、税收与社会保障等制度环境中(吴清军,2025)。
参考文献
周亦垚,蓝江.《资本主义的雅努斯:资本抑或云地租——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资本论>的误读》,《探索与争鸣》2024第8期。
Cédric Durand. 《Scouting Capital’s Frontiers——Reply to Morozov’s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New Left Review》2022年第3期。
许怡.《“机器霸权”的建构与解构:基于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案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辑。
张兆曙,高远欣.《“刷单炒信”与平台市场的“技术-市场悖论”》,《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赵磊,杨伟国,陈龙.《互联网平台劳动力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与机制——一个“动力—能力”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3期。
吴清军. 《平台用工的商業模式與治理困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25年第2期。
书籍信息

《技术封建主义》
[法] 塞德里克·迪朗 著
陈荣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定价:69.00元
ISBN:9787300328508
作者简介
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数字经济、金融资本主义、技术政治与全球经济体系转型等,是当代激进经济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近年来致力于探讨平台资本主义、算法控制与数据垄断的社会后果。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与巴黎第十三大学,现为巴黎政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代表作包括《资本主义的未来》《福祉经济学批判》等,其相关研究广泛发表于《新左评论》《月刊评论》等欧洲批判性学术刊物。
译者简介
陈荣钢,云南曲靖人,现任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悉尼大学研究型文科硕士,同济大学文学学士。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图像、媒介和文化/社会/历史的交叉领域;华语电影研究;大众文化对媒介与技术的想象;电影的历史再现;运动影像的历史编纂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YAsbPzhA4f_fgE7CEt2qA